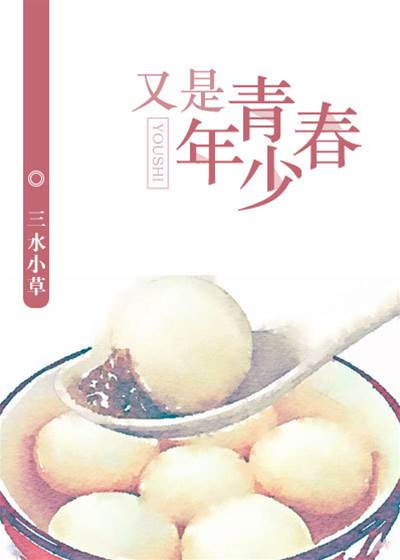《告別天堂》 第1章 回到最初的地方
把頭枕到我口,“你學什麼的?”“中文。”“中文?”重復,“很有意思吧?”“可能。”我答。我是真的不確定,我很去上課。“你呢,你學什麼?”我問。“會計。”我同地看著,“無聊嗎?”“嗯,不過,”停頓了片刻,“學這個,你能明白一點咱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流程,像學中文就未必……不對,我是說,會計這東西,能讓你覺到自己在維持這個‘社會’運轉。反正……你是中文系的,一定比我會形容。”我看著,“我懂。”
我還以為接下來我們又要開始瘋狂,但是沒有。我們倆就這麼聊了一夜。我長這麼大從沒說過這麼多的話。天亮時心滿意足地嘆著氣,“我要是個男人,現在就跟你義結金蘭。”
后來我就天天去找,和上床無關。這世上有比做更重要的東西。可惜你不能指所有的人都明白這個。我相信,現在要是有人跟我的一些大學同學提起“周雷”這個人,他們保證會說:“就是那個對一個婊子認真的可憐蟲。”
二○○○年的九月,一個夜晚,天上下著煩人的小雨。我們這兒不是江南,這天氣并不常見。我依舊窩在宿舍里看碟。上鋪的兩個哥們兒聊天的聲音有一句沒一句地鉆進我的耳朵。“靠,這人打起來,也真夠瞧的。”“可惜咱見不著。”“不過,小惠形容得也夠生的了。馮湘蘭的頭發被拽下來一大把……”我“騰”地坐起來,頭當然撞到了床架上。“你們說什麼呢?!”我大聲問。
我只穿著拖鞋,三步并作兩步地往樓下沖。后傳來那個北京人幸災樂禍的聲音:“瞧他丫的。”
Advertisement
其實事很簡單。無非是生宿舍誰的東西放錯地方了。關鍵是,那些生早就看馮湘蘭不順眼,馮湘蘭只是跟其中一個了手。其他幾個原本是拉架的,最后卻變了幾只母狗群毆馮湘蘭,而且還把的東西扔到門外滾。真他媽——我看見了。
就在我們樓下。坐在一塊雨水淋不到的地方,靜靜地看著我。頭上凝著一層雨霧,脖子上和臉上都是讓指甲抓傷的痕跡,灰的從大破到腳踝。站起來,眼睛定定地住我,說:“周雷,除了你,我想不出來該找誰。”
我抱住了。
那景一定很稽,一個穿著拖鞋汗衫頭發蓬的男人和一個傷痕累累狼狽不堪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忘形地抱著。他們不是俊男,他們的姿勢很笨拙——過路的人都在看這個笑話。可是,這些閑人,關心過什麼呢?全是看客,現在的小事如此,大事,亦然。
“聽我說,”我告訴,“咱們不住那個鳥蛋宿舍了。咱們去外邊租房子,咱們倆,只有我和你。別跟那些人一般見識,們是一群母狗。因為沒男人要所以沒地方發……”我知道我又在說蠢話。
可是抬起頭,帶著一臉的淚笑了,“你說得對。”
天楊,那個時候我想起了你。為什麼呢?大概是我還以為,我要和過一輩子了。于是你的臉就閃現了出來。于是我心里又是一。可是,那個時候,我除了抱,又能怎麼辦呢?
我和馮湘蘭同居以后,再沒和別的男人睡過覺。不過這幸福生活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我們畢業了。什麼都不用多說,我們都不是不懂事的人。有一天我一覺醒來,發現的東西都不見了。這正好,我們都不喜歡慘兮兮的告別。付清了我倆拖欠了幾個月的房租,知道我沒錢。還留下了泉州家鄉的地址和電話。的便條上說只要我有困難,打這個電話就聯系得到。
Advertisement
然后我開始了我的漫游,幾年來,我在北京租過地下室,在廣州的一個四星級酒店里一邊端盤子一邊留意報上的招聘廣告,在長沙我的第一個月的薪水被人走,好不容易,我有了都的這份工作。雖說是個袖珍廣告公司,可我大小是個“創意總監”。因為馮湘蘭的喜帖,一切又得從頭開始。我反復研究著這張紅請柬,真詭異,人居然在重慶,嫁得夠遠的。
天楊,我于是又坐上了火車,目的地是我們的故鄉。真奇怪,我考上大學的時候發誓不再回去的,我實在厭倦了那座城市污濁的空氣,像所有工業城市一樣沒有想象力的布局,難聽的方言,滿大街不會穿服的人,當然還有永不缺席的沙塵暴。可是我發現,當我賺到了幾年來最多的錢,我卻早已失去了落魄時對這個世界的希和夢想。
上一次見到你是在廣州吧?純粹是一場巧合。是大學剛畢業那年的夏天,我在一間小冰店看見你。你說你是來你姑姑家玩,你九月就要上班,這是最后一個假期。那時我真驚訝你選擇了回去,我還以為你和我一樣,打死要在外面漂著呢。
在火車上我夢見了你。你停頓在一片夕的輝之中,是我們學校的籃球館,木地板散發著清香。你一個人坐在看臺上一排又一排橙的椅子之間。兩條麻花辮垂在前,藏藍的夏季校服拂著你壯壯的小。籃球一下一下地砸著地板,空曠的聲音,你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孤獨的籃球架。天楊,你不知道你自己很。
然后,我醒了。火車寂靜地前進著。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我以為我自己不該屬于我們的故鄉,我以為我就應該背井離鄉去過更好的日子,卻不知道是咱們紅花崗巖的母校把這種驕傲植我的。而我,我曾經恨這個學校,把它當故鄉的一部分來恨的。
Advertisement
天楊,那個時候我真想你。想看看你,看看你還是不是那個兩條麻花辮,小壯壯的傻丫頭。于是我來到了這里,長長的,寂靜的走廊。你出現在另一端。無打采,步履蹣跚,就像幾年前不知道自己很漂亮一樣,不知道自己已經風萬種。你說:“了吧?火車上的東西又貴,你肯定吃不飽。”你這句話險些催出我的眼淚,天楊。
[天楊]
我把他帶進了家里,打開客廳里的燈。他說:“一點沒變。”
爺爺出去玩以后,我也給劉阿姨放了假。我每天的晚飯都是打電話樓下一間新開的小館子的外賣。今天我多要了幾個菜,當然還有啤酒。他假惺惺地說不用這麼破費,還是把七八個一次飯盒一掃而。
“我可以煙吧?”我問他。
他愣了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煙的?”
我點上一支,問他:“你要不要?”他搖頭,又作痛惜狀地嘆氣,“白天使也這麼頹廢——真后現代。”
“我又從來沒當著病人面。”我說。
“你和你男朋友,怎麼樣了?”他喝了一大口啤酒,使用著一種滿足的腔調。
“你指哪個?”我問。
“最近的那個。”
“上個月剛散。不然還能讓你見見。”
“饒了我吧,你的品位。”他笑。
“你還記得林薇吧?就是初中時候咱們班的。”我說。
“記得,怎麼,結婚了?”他嚼了一的宮保丁,口齒不清。
“你怎麼知道的?”
“這不難,”他看著我,“聽你的語氣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麼。”
“跟你說話真沒勁。”
“說吧,林薇結婚了,然后呢?”
“沒什麼。我那天在現代購中心上和老公,正買DVD機呢。那個男人,丑得我都不忍心多看。”
Advertisement
“你呢,不管怎麼說人家是嫁出去了,你不急?二十五了。”
“二十四。三個月以后才二十五。年輕得很呢。”
“等你急了的時候就考慮考慮我吧。”他說,“反正你早晚都要嫁人,不如嫁個人。你說呢?”
“吃你的。”我拿筷子敲敲他的頭。他繼續狼吞虎咽,一時間滿屋子的寂靜。我拆開了父親的信。
“你爸他老人家還好?”
“好。”我簡短地說。
父親的信上說,兩個月后他又要去非洲,這一次不能把小弟弟放到他媽媽家,因為那個時候要結婚。所以,兩個月后,我就會見到這個小家伙。他有個奇怪的名字,易克宋,小名不不。
“怎麼了?”他問我。
“沒有,”我說,“你吃好了嗎?”
“好得都了。”
“那早點睡吧,你就住我爸爸的那間房,想洗澡的話,用那條墨綠的浴巾,明兒我還得上班。”我把煙按滅了,重重地嘆口氣。
“我不困,想去肖強那兒租點碟。”
“你不知道?他把那間店關了。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沒,看著我。
“怎麼了?”
“天楊,”他慢慢地說,“這幾年,你過得好嗎?”
“怎麼突然這麼煽?”我笑笑,“我爺爺兩個星期以后才回來呢,你放心住在這兒。我可以先借你點錢,正好我剛剛發薪水,不過你一找到工作就馬上還我。”
他說:“。”
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我去上班,他留在家里上網,還順便幫我打掃打掃家,做做早餐什麼的。表現不錯——第一天早上就把我積了一池子的碗碟都洗了。他并不急著找工作,也不急著跟他父母聯系。很奇怪的,剛剛三天我就習慣了他的存在,好像他本來就是個家庭的員一樣。有天黃昏我們一起去超市采購,又到了老年癡呆的前任院長。他熱地沖我們走過來,跟周雷握手,“哎呀,好久沒見你了。你都結婚了?回去幫我問你媽好,告訴要多鍛煉……”周雷居然和我一樣笑容可掬地說他一定轉告。
方圓的況這個禮拜出人意料地穩定。而且,白球的數量還有所上升。媽媽的臉上終于有了點和笑容。龍威和袁亮亮還是一如既往地“不像癌癥患者”,皮皮還是一如既往地酷,病房里又住進來一個四歲的小姑娘。準確地說,下個月才四歲。一對鼓鼓的小金魚眼。興地用父親的手機跟講話:“,我是白病,我不用去兒園了!”也許是春天的關系,病房里傳遞著一種難得的輕松和愉快。晚飯后,那些陪床的父母也開始在臺上打打撲克什麼的。總之,日子呈現出一種充滿希的表。或許是假象,但終究令人心曠神怡。只有一次意外:某天中午周雷突然沖進病房,惹得楊佩一干人側目,他滿臉驚慌,“怎麼辦天楊?你爺爺回來了。”
“‘天楊’,”楊佩竊竊私語,“得還真親切。”
結果到了下午,我去給袁亮亮輸的時候,在走廊上就聽見這對活寶拖長了聲音喊:“天——楊——,天——楊——”。
該死的楊佩。
[周雷]
天楊,你瘦了。你原來是個的小丫頭。十三歲那年,還沒發育,像個小水蘿卜,在教室的第一排。可是自從你遇到江東,你就瘦了。等大家注意到你的消瘦時,你已經十六歲,讓你一夜間亭亭玉立。現在你二十五歲了,這消瘦就跟江東一樣,印在你的皮里,變組合你生命的DNA碼,無聲無息。
咱們不說江東那個狗雜種,我知道你已經忘了他了。沒有人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還忘不了十五歲那年的人——除非他十年來沒進化過。可是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很多表,很多小作,都是跟江東在一起的時候形的。比如你歪著頭,有點嫵地笑笑;比如你垂下眼睛,凝視自己的指尖的樣子;還有你的口頭禪“你去死吧”,諸如此類的細節是江東刻在你靈魂中的簽名。這讓我無比惱火,可又無法回避。
你去上班的時候,我想要整理你的房間。書架上的書幾乎都換過了,只有《加繆全集》和《海子的詩》還在。我把那本《海子的詩》出來,那里面有你十二年來畫下的深淺不同、細不同的紅線。
“五月的麥地上天鵝的村莊,沉默孤獨的村莊,一個在前一個在后,這就是普希金和我誕生的地方。”
“看見了嗎?那兩只白鴿子,它們是屈原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讓我們,我們和河水一起,穿上它們吧。”
“珍惜黃昏的村莊,珍惜雨水的村莊,萬里無云如同我永恒的悲傷。”
。這孽障,寫得真好。
我還記得那個下午,天楊,你就坐在這間小屋里給我讀這本書。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當年最喜歡的句子。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然后你突然靠近我,你說:“周雷,要是海子還活著,我長大以后要嫁給他。”
我本來想說不會吧他長這麼丑,可是天楊的拳頭不輸后來聞名亞洲的野蠻友,于是我說:“就算他還活著,可要是他有老婆呢?”
“我不管。”
“要是他不想娶你呢?”
“我不管。”
天楊,那時我們才十四歲,你很快就會遇上江東。
好吧,既然江東是繞不過去的,那麼我晚些再提到他總可以了吧。
日子安寧地流逝著。我在家——是天楊家每天上網聊天,喝罐裝啤酒,也看碟。晚上和天楊一起吃外賣。吃完了,自然是我洗碗。生活過到了另一種境界:不再看手表,也不再看日歷。
某個午夜,我聽見房里傳出來一陣夢魘的囈語。我走進去,打開燈,推醒了,“天楊,天楊你做夢了吧,天楊——”睜開眼睛,愣了一秒鐘,笑了,“我做了個夢,怪嚇人的。”的臉頰著我的手背,臉紅了,“周雷你能陪我待會兒嗎?我睡著了你再走。”
“當然。”我坐在的床沿上。穿了件乖孩的睡,印著櫻桃小丸子的頭像,頭發上的香波味鉆進了我的鼻子里,的。我嘲笑自己,“裝他媽什麼純啊,一把年紀了又不是個雛兒。”
“周雷,”的往里錯了錯,“你要是困你就躺上來。”
“不好吧。”我裝正直。
“咱們小時候不就是這樣睡覺嗎?兒園里,你忘了,你的床挨著我的。”
“記得。我經常做鬼臉逗你笑,看見老師過來了就閉上眼睛,結果每次挨罵的都是你。”我于是也躺了上去,我的臉著的后腦勺。
我忘了聲明,這是張單人床,所以我地著并不是為了占的便宜。轉過了子,我還從來沒在這麼近的距離下注視。說:“周雷,再過兩個月,我爸爸要把不不送來。我心里有點。”
“睡吧。”我關上了燈。
我輕輕地擁著你,天楊。你的呼吸很快變得平緩而沒有知覺,那是睡著了的人的氣息。睡是死的兄弟你明天早上才會活過來,小笨蛋,你就不怕我襲你。現在你就在我跟前,你的臉在我的口,你上有牛的氣味。我想你做夢了,因為你突然間抓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你睡覺居然有磨牙的習慣,丟人。
看著你睡的樣子,我TMD沒有一。
又是一夜沒睡。這滋味并不好。想想看,八個小時,躺著什麼都不做是件傷神的事兒。除了“回憶”你還能做什麼?你總得找點事干干。于是我就開始回憶。直到天一點一點地亮起來,直到外邊的街道上傳來人群的聲音,直到你睜開眼睛,怔怔地問我:“幾點了?”
我是在你出門之后才迷迷糊糊地打了個盹兒,臨近中午時走出房間,看見客廳里有一對面目慈祥的老爺爺老疑地看著我……當然,這是后話。
還是回到上一個夜晚吧,我用了八個小時來“回憶”——這在現代社會簡直是犯罪行為。我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回憶十三四歲的我們,兩個小時來回憶我的大學時代,剩下的四個小時——是黑夜里最微妙的時段,看著黎明像個蒼白的怨婦一樣來臨,這四個小時留給江東——我是說那場以江東為起因,把我們每個人都卷進去的磨難。比如天楊,比如我,比如肖強,比如方可寒。
猜你喜歡
-
完結641 章

我和影帝隱婚的日子
還在念大三的宋喬,偶然的機會被星探發掘,作為新生代小演員進入星娛傳媒,從此踏上了星光之路!…
115.6萬字8 9365 -
連載519 章

重逢后大佬盯上了她的崽
被雙胞胎渣妹算計謀害,懷孕后被迫遠走國外。 四年後,她帶著一雙天才寶貝回國。 重逢后。 男人盯著兩個縮小版的自己,強硬的把她堵在角落,「女人,偷生我的崽是要付出代價的」 姜黎心虛,「……你想怎樣?」 「我記得你罵我弱雞」 男人冷笑,「那就再生一個,證明一下我的實力」 「……」
89.8萬字8 40813 -
連載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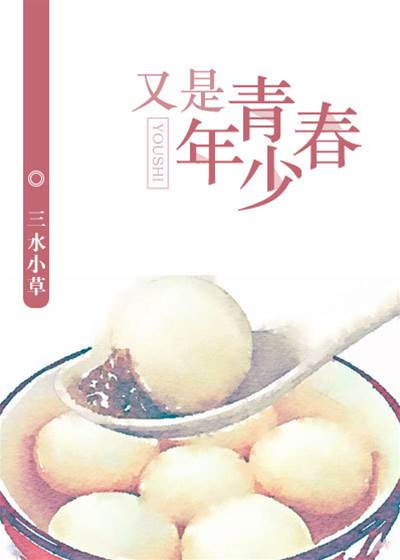
又是青春年少
沈牧平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問沈小運: “想吃點什麼?” 沈小運每天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在下班的時候告訴沈牧平: “今天有人給我特別好吃的點心,我都吃了,沒給你留。” ———————————————— 時間是一個無聲的環 我不怕在這環中忘卻自己曾經的所有擁有 卻怕最后的生命 沉默 死寂 枯竭 仿佛那河水 只是路過了一聲又一聲的大船鳴笛 ——僅以此文,寫給一群在遺忘和被遺忘的人 ———————————————— 寫給世界上所有的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寫給所有的成長和老去。...
12.9萬字8 303 -
完結434 章

誘妻入懷,狼性前夫靠邊
她是天下第一神偷,可哪曾想,有一天她會被一個男人偷播了種。 關鍵的關鍵是,懷胎八月辛辛苦苦生下的寶寶,竟然也被那個男人偷走,是可忍孰不可忍。 時隔五年之后,成為娛樂巨星的她再次回歸。 “男人,你欠我的,我要一步一步拿回來。” 開玩笑,她是誰,絕世神偷。
123.2萬字8 3037 -
連載148 章

顧總,你老婆又被黑了
出道第一天,因為她“絕美”的外表,她迅速躥紅且黑料不斷。 潛規則,當小三,花瓶無演技…… 只有想不到,沒有黑粉做不到。 從此,葉清淺在“黑紅”這條路上一去不復返! 卻不料,有小蘿卜頭突然冒出來抱著自己大腿叫“媽咪”! 還有霸道總裁一臉寵溺,“你想做什麼盡管去,我和寶寶會是你最堅強的后盾!” 葉清淺炸了,“我單身,單身!”
35.3萬字8 303 -
完結1162 章

總裁在上
“偷走我的基因,就想走?”他抓她,逼她交出3年前生的寶寶。沒生過?那就再懷一次!偏執狂總裁的一場豪奪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淪陷。OK,寶寶生下來交給他,她走!可是,他卻将她五花大綁扔到床上,狂燒怒意,“女人,誰說只生一個了?”
254.1萬字8 37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