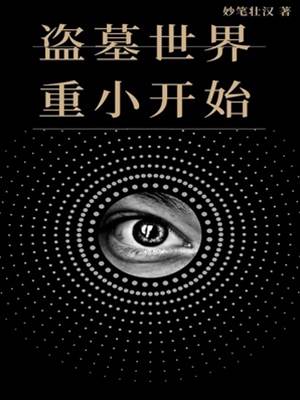《狐說魃道》第五章
穿過三重院落,再沿著一條被大片竹林遮得幾乎看不清楚路的小石子道向北,再走三五分鐘路景能看到一片池塘。池塘不大,被三條長廊環繞著,差不多也就一個院子的大小。中間有塊長滿了青苔的假山,依稀可以看到上面大大的,還沒褪陳年老漆的三個草字——‘荷風池’。
本新伯說荷風池是易園里最有特的景點之一。
顧名思義,荷風池就是一個種滿了荷花的池子,不過可能花期還沒到的關系,雖然已經算是夏了,我到了之后沒看到一朵盛開的荷花,有的只是一大片一大片墨綠的荷葉和花苞,在下午好容易出一角臉的慘白里有點疲憊地擁在枯萎的浮萍上,一層疊著一層,把水面遮得嚴嚴實實。偶而風吹過,那些厚厚的葉子抖出沙沙一陣清冷的碎響,而樹上的麻雀也跟著嘰嘰喳喳鼓噪起來,鳥聲和碎響聲,讓這片空一無人的地方聽起來熱鬧非凡,可是也僅僅是聽上去而已。更多的是一種奇怪的空虛,不論是景還是風景。
本新伯說得不錯,沒什麼地方能比這里更適合打發午后一個人的無聊時間,只需要往池塘邊的長凳上一躺,那些從池子里散出來的干荷葉的味道,和背后那片被太曬出來的微燙,就足夠讓人到眼皮子發沉。
我找了條還算干凈的長凳坐了下來,打開手機看了看,里面沒有狐貍發給我的留言,于是躺下準備小睡上一會兒。可是周圍的聲音和線一時又讓我很難睡,它們是那樣明亮和吵鬧,即使閉著眼睛也像群不安分的靈在你眼皮子和耳外舞。于是只好睜著雙眼干看著池子里那些濃的植,看它們蓬張揚著它們旺盛的生命力,從很多年前開始一直持續著的重復的過程。
Advertisement
忽然想起它們或許是這房子里最持久也最鮮活的見證者了,雖然看上去那麼而脆弱,但即使是房子都在逐漸老去,惟獨它們依然是年輕的,每一年生長開花,每一年靜靜目睹著這里的是人非。更有甚,在它們前一刻的記憶里,坐在我下這條凳子上的還是些梳著油可鑒的頭發,穿著錦華服的男,轉眼卻了我這麼個和周圍一切格格不的人,而這條長凳又曾經有多人坐過?他們有著什麼樣的份,什麼樣的心思……
這念頭讓我覺得有趣了起來,它就像一個漫不經心間把一些流逝的東西抓住并給你看的小小魔,你能呼吸得到它,覺得到它,但無法它。這種覺實在是妙不可言。然后我忽然留意到了一些劃痕。
就在我眼前那柱子上,一轉頭就看到了,那些斜斜的一行連著一行的痕跡。不過這發現起先并沒有讓我太在意。畢竟這種老掉牙的木頭上有再多的痕跡,都是不會讓人覺得突兀的,那些草草的痕跡和柱子漆水班駁的表面混雜在一起一點都不起眼。
直到后來我突然意識到,那些七八糟的劃痕都是些文字。
字跡潦草簡單,并且著點稚,它似乎是首不知道在哪一年被哪個調皮的小孩用刀子刻上去的兒歌。我仔細看了一下,它們這麼寫著:
木頭娃娃著腦袋
搖啊搖啊什麼也看不見
你拍一下我拍一下娃娃出來
最慢的一個娃娃在……
最末那行字的尾部看不到了,似乎是被刻到了柱子的背面,我忍不住爬起依著它們朝后看過去。但柱子背面什麼文字都沒有,那里只是一大塊快要剝落的漆皮。
我出手指在那上面小心刮了刮。
Advertisement
干燥的涂料隨著我的指甲一點點從柱子上剝落,片刻約看到里面有劃刻的痕跡,就在這時,我頭頂上突然響起一陣啞嚨人尖笑般的聲音:
“呱啊!”
我的手一抖。
抬頭看到只漆黑的鳥從天而降落到對面的廊檐上,一邊抖著,一邊張開大再次發出那種讓人骨悚然的聲:“呱啊!”
我認出它是烏,那種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是看不到的鳥類。第一次不是通過屏幕而是真實地見到這種,它的個頭比我想象中要大,并且丑陋。聲和電視電影里那種配上去的聲音不太一樣,更尖銳,帶著種沙沙的音,每一次都能讓人聽得一激靈。
第二次尖后它住了,然后合攏了翅膀蹲在廊檐上一不看著我,像團漆黑的臟東西。我沒理它。凡是那種丑陋并且格詭異的鳥類都讓我覺得不舒服,比如麻雀,比如貓頭鷹,比如烏……于是回過頭繼續用指甲剝著柱子上的油漆。而越往下那些漆水越是難剝,因為它是完全在柱子上的,我不得不加大了力道往下摳。
說不清為什麼,那下面也許什麼都沒有,也許有的不過只是那首短短謠里某幾個毫無意義的字,可我非常想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呱啊!!!”突然又是一聲尖。
眼角瞥見那只漆黑的鳥突然翅膀一張朝我方向直飛了我來,我大吃一驚。忙跳下凳子試圖躲開,手一卻把手機甩進了水池。這當口一陣冰冷的風從我臉旁刮過,沒來得及反應過來這意味著什麼,我邊上那柱子上砰的發出聲悶響。
然后一些溫熱的東西濺到了我的臉上,我看到一只凌不堪的黑翅膀在柱子背后痙攣似的抖著,一邊扇出些凌得讓我腎上腺素急增的聲音。
Advertisement
片刻聲音停了,那翅膀從柱子上了
下來,通的聲掉進池子里,就是剛才我手機掉落的位置。沉下,再浮上,出一只巨大尖銳的啄,還有半邊模糊的。
那只剛才突然間莫名俯沖向我的烏……
腦子里有什麼東西尖銳地了一聲,沒再管掉進池子里的手機和柱子上那片被我刮得差不多了的油漆,我拔朝著走廊外倉皇奔了出去。
才奔出那條狹窄的石子路,耳邊一聲驚,我同眼前突然出現的一道人影一頭撞到了一起。瞬間天旋地轉,我和那人同時摔倒在了地上,與此同時遠一道咆哮般的大嗓門響起:“卡卡卡卡卡!”
這才看清了周圍逐漸聚集過來的人群,還有被我在下的梅蘭那張驚得有點扭曲的俏臉。我急忙一骨碌爬起來,手想起扶,已經被邊上的工作人員圍住,一個個帶著又怒又疑的表看著我,像是怕我再次莽撞地傷到似的。這讓我恨不得找個地鉆進去。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隨之一陣啪踏啪踏的腳步聲由遠到近,撥開人群,劇組導演那張怒獅子般的臉再次出現在我眼前:“我姥姥的怎麼又是你,大姐,你存心跟我過不去是不是?!”話說到這里突然停住,然后轉過臉用手里的本子朝梅蘭頭上敲了一記:“快看好臉上的表!就是這表!我要的就是這種表!”
瞬間我的臉再次了所有人注目的焦點,而我惶惶然不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直到梅蘭注視著我的那雙眼由原來的迷逐漸變了一種驚訝,再到驚恐,再逐漸擴散到臉上每一道廓,我被這表給嚇了一跳。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驚到了,正下意識了自己的臉,那導演卻笑了:“ok!很好,就是這樣!”然后轉過頭再次看了我一眼,這次不再像只發怒的獅子,但嗓門依舊洪亮得像是在訓人:“你怎麼啦丫頭,活見鬼一樣。”
Advertisement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總不能說,我是被一只死烏給嚇出來的,這會被他們當笑話吧。可他盯著我看的樣子又讓我覺得如果不為剛才的行為解釋些什麼,他不會輕易放我離開:“我在找廁所。”口而出:“這里好多屋子都上了鎖,我找不到我那屋在哪里。“
這回答讓他頗意外,因為他的眉皺了起來。幸好沒等他繼續問,一旁有人對我道:“往左邊直走有道門,出去右轉那里有個公廁。”
循著話音我看到了靳雨澤那張麗的臉。他遠遠站在攝影機的邊上,里叼著支煙側眸著我,眼里閃爍著什麼似有若無的東西,這讓我不自懷疑他是否看穿了我小小謊話里那點貓膩,不過還是很快激地朝他點點頭。這當口沒人再理會我了,因為主角抓到了角的表,這讓導演急著開始繼續拍,于是在他們忙碌著重新布置位置的時候我按著靳雨澤指的路跑出了這個地方,當然沒按他所說的繼續朝右轉,而是往左返回了我住的那個院子。
因為挨得近,進大院后我還能聽見那導演獷的嗓門在拍攝指揮。他實在是個力超級旺盛的老頭,而且還是個居然有臉皮我大姐的老頭。時不時還能聽到助理們跑的聲音和演員的尖。他們這一整天似乎都在拍攝主角到驚嚇的戲。
當然這些嘈雜并沒有讓我覺吵鬧,反而讓我從之前的驚恐里恢復了過來,因為我總算不再滿腦子都是那只鳥死掉時奇丑無比到令人惡寒的樣子。不得不說剛才我真被那只烏給嚇到了,那只對我來說簡直比地獄里爬出來的鬼怪還要可怕和惡心的生。它讓我一度忘了自己其實遠比它大得多,并且強壯得多。
只不過一眼而已,它滿臟的羽和那雙死了還像有靈魂般死死瞪著我的眼就把我徹底給嚇得了方寸。更糟糕的是我還把我的手機給弄丟了,那只花了我兩千多塊錢剛剛買回來的、用了還不到一個月的手機。被這麼只丑陋的小鳥一嚇,就這麼沒了。如果讓狐貍知道這一切他會笑死我的,我敢保證。
琢磨著正準備進屋,一腳進去我又退了出來,說不出的一種覺,我覺得背后好象有什麼人在看著我。
可是回頭看又什麼都沒有。后空的,只有一棵兩人合抱那麼的老梧桐在院子中心站著,頭頂的葉子幾乎能遮掉院子的半邊天,風一吹葉子聲波濤翻卷。
那麼那種奇怪的覺到底是什麼?我猶疑著朝兩邊再看了看,然后看到了昨晚那間似乎有人影跑進去的房子。它同我的房間之間隔著道天井和這棵老樹,白天看來倒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門窗依舊閉著,應該很久沒人住了,上面蒙著層細細的灰。窗玻璃上依舊靠著昨晚見過的那只木偶,它還在。
不知怎的,在看到它之前我對它的存在并不報任何期。所以它在倒反而讓我有點意外。這只小小的、淡黃的木偶,應該是件很老很老的玩了,糙得像某件剛從墳墓里挖出來的文。而掉了漆的表面讓它看上去更加丑陋和可憐,五幾乎已經分辨不清楚了,只有模糊的一點廓可以區別出它的眼睛和。它靜靜在玻璃上,像個希鉆出來到走走的孤獨的孩子。
這種奇怪的覺讓我不由自住轉過朝那間屋子走了過去。
近到門前那扇閉著的門突然嘎地聲開了,雖然只是開了道小小的,這讓我吃了一驚。趕朝后退,一邊慶幸自己還沒那麼沖。
這房子有點不對勁,直覺這麼告訴我。
正準備不再去理會徑自返回自己的房間,可是跟著一陣細細的鈴音從屋子里傳出,悉的音調讓我幾步上前一把將門推開。
猜你喜歡
-
完結525 章
家有貓妻
外婆從後山荒墳那抱回來兩隻大小黑貓,讓我叫大黑貓媽,還讓我和小黑貓拜天地,從那之後
108.5萬字8 2717 -
連載1299 章

神秘復甦
五濁惡世,地獄已空,厲鬼復甦,人間如獄。 這個世界鬼出現了......那麼神又在哪裡? 求神救世,可世上已無神,隻有鬼。
369.7萬字8 4991 -
連載58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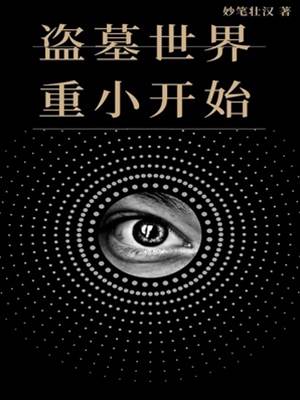
盜墓世界重小開始
重生幼時,本想擬補前世遺憾,讓家人過上幸福的生活。然得家族傳承,后發現是盜墓世界,沒想下墓的他,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下墓對他的幫助,于是開始了探險之旅。
107.9萬字8 4241 -
完結1059 章
請叫我鬼差大人王燁張開
永夜過後,恐怖復甦。十里荒墳,詭異的歌聲。尋找雙臂的老人,無頭的嬰兒... 他們不停的拼接著自己的身體,爆發出更恐怖的氣息。荒土中,一隻斷手,都可以毀天滅地。在這種黑暗,絕望的環境下,一座若隱若現的郵局... 一名神秘的年輕人,一輛行駛於虛空的郵車... 一封又一封血紅色的信件,成為了人們口中的禁忌... ————鬼差。 PS:無女主或者單女主(不要亂猜,至少不是周涵)
180.2萬字8 25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